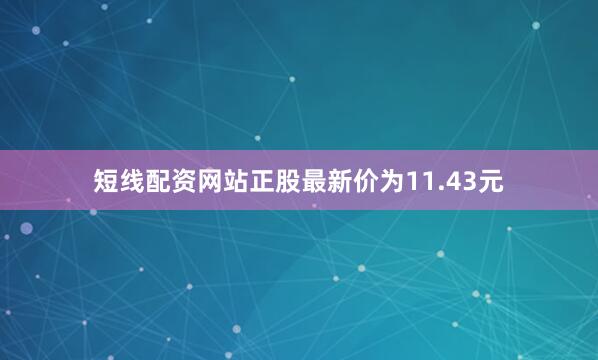1938年,梁漱溟造访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向毛泽东推荐了自己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并坦诚地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不认同。毛泽东细致地批注了这部著作,并与梁漱溟就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尽管双方观点相左,彻夜长谈却未能达成共识。然而,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的言辞让梁漱溟如沐春风。离别之时,毛泽东巧妙地通过荐书的方式,点出了梁漱溟认识上的误区,从而促使其认知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此事堪称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之作。
梁漱溟向毛泽东推荐《乡村建设理论》。
“本书(《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理念,其雏形起源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日基本成型,最终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得以成熟。”这部著作凝聚了梁漱溟的诸多心血。他对自己的理论著作亦颇为自信,特取副标题为《中国命运之前途》。然而,日本对山东的入侵,标志着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
梁漱溟对我国的抗日形势深感忧虑。鉴于此,他前往延安,向中共的领袖们请教关于国家命运与未来的问题。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梁漱溟,并耐心倾听了他的讲述。在详细了解梁漱溟的顾虑之后,毛泽东坚定地回应说,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中国必将取得胜利,日本必将败北。梁漱溟对此深感信服。首次长谈结束后,梁漱溟将自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予毛泽东,期待下次能就这本书进行深入的探讨。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分为“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两大篇章。他指出,我国正面临着文化失衡的困境,而解决之道便是通过乡村建设孕育新文化。具体而言,他提倡将“消极的相互关怀”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实践”;这体现在乡约精神中的“患难相恤”,如应对水火、盗贼等问题。我们主张未雨绸缪,而非等到灾难降临后才进行援助。例如,面对贫乏问题——我国人民的一大难题,我们应倡导合作生产和销售,而不仅仅是消极地救济贫困。这一理念与乡约的本意相契合,并无冲突。乡约虽注重消极的相互关怀,但我们更倾向于将其转化为积极的行动,预先防范问题的发生;最佳状态是防止问题产生。比如,我们应建立健全的自卫组织,预防盗贼,将水患救济转变为水利建设,这些都是乡约所倡导的。在乡约中,对各类事务均有周到的考虑——如患难相恤的七项内容,只是略显消极。我们则将这种消极的相互关怀转变为积极的行动。我国古人对于生活的方式,不太追求过分进步,如手推车、牛马车等,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汽车、火车。这种态度在乡约中也有所体现。我们则主张积极进取,在积极行动中蕴含着追求进步的意义;因为积极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未能取得预期成果,但他对自己的理论依旧深信不疑。他立足于传统士大夫的视角,竭力凸显“士”阶层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士人位居四民之巅,象征着理性,肩负着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四民之间交流互融的重任。基于此,他认为“中国社会实则是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中,固然存在贫富、贵贱的差别,然而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人们可以相互流动,形成对立的阶级格局并不明显,故不能称之为阶级社会”。因此,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共产党的失误在于照搬外国阶级社会中的农民运动模式,未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当今中国社会亟需整顿与改造,而非进行阶级革命;农民的地位亟需提升,而非彻底翻身”。

1937年,毛在延安凤凰山。
熟谙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洞察的毛泽东,显然无法苟同梁漱溟的观点。在激烈的论辩中,毛泽东坚信中国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而梁漱溟则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梁漱溟对此表示异议,并指出毛泽东过于关注社会的一般共性(即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共有的阶级对立、矛盾和斗争现象)。在那个时代,抗日救亡成为头等大事,因此,两位伟人的争论并不急于得出结论。当梁漱溟离开延安之际,毛泽东特意向他推荐了《反杜林论》。
毛泽东推荐梁漱溟读《反杜林论》是为深化其理论修养。
毛泽东建议梁漱溟深入研究《反杜林论》的哪一个部分。
杜林曾于1867年著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起挑战,但转至19世纪70年代,他突然转向信仰社会主义,并提出了一套全面而细致的改良主义理论。恩格斯随即对杜林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撰写了《反杜林论》。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从哲学层面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形而上学以及唯心史观,同时捍卫并阐述了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反映论,以及唯物史观的阶级论、道德论和平等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恩格斯对杜林的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对“暴力决定论”的批判,并正确地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假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并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方法论,清晰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此可见,《反杜林论》对梁漱溟而言,无疑是一本至关重要的著作。从身份和思想状态来看,梁漱溟与杜林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声称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仍然保留着旧有的世界观。他们的目标并非摧毁旧世界,而是通过妥协与调和来修补它。

“贫富贵贱即是阶级差异”,“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共享财产、不相互关照、不相互负责。贫民生计问题毫无保障,只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而梁漱溟所提到的“共产”,也“只是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之上的家庭共产主义”。“富人的财富不允许穷人消费。”这种伦理政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封建剥削,而非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而是让地主阶级得以安宁,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不安之中。不是让每个人都做到最好,而是让统治阶级做到最好,而被统治者则陷入极度的困境。毛泽东向推崇改良主义的梁漱溟推荐《反杜林论》,其用意不言而喻。
“正因其貌似而非,故能不革命而自诩为革命者。”

◆梁漱溟
梁漱溟坚决否认中国属于阶级社会,因此对暴力革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阐述了暴力的多重作用,其中便包括革命的力量。他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暴力,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是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催化剂,而且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借助武力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打破僵化、麻木的政治格局……”毛泽东之所以推荐此书,正是希望梁漱溟能够认识到暴力革命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教诲,实则深藏于《反杜林论》一书中。显而易见,毛泽东对两人争论的核心以及梁漱溟思想失误的根源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巧妙地运用荐书的方式,委婉地指出了梁漱溟的错误及其成因。毛泽东之所以让梁漱溟研读《反杜林论》,正是希望他能够借此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伦理为本还是阶级对抗?
那么,我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还是以阶级为特征?
“在外人面前不要说姐姐是上吊死的,就说她是跌死的。”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亲眼目睹社会问题,亲眼看到环境如何将人逼至绝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淡漠,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也能变得如此冷漠无情。然而,类似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却十分普遍。

◆毛泽东与梁漱溟。
实际上,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亦是对毛泽东观点的有力佐证。山东军阀韩复榘深受梁漱溟影响,在山东逐步实施“政、教、养、卫合一”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乡农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亦服务于政权,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并具备武装力量,学校内设有枪支。据《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的主编、北大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回忆,梁漱溟在邹平以自卫为由组织民众武装,其中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则投降日寇,沦为汉奸。当地民众对此痛恨至极,甚至有乡建干部被群众杀害。梁漱溟虽出身北方官宦世家,自幼生活在北京,却从未真正体验过农村生活,自然无法深刻理解旧社会的残酷无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梁漱溟都将阶级社会包裹在温情脉脉的“伦理本位”之中。然而,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必须撕下统治阶级的伪装。归根结底,共产党人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梁漱溟则代表着“士”的利益,以及统治阶级的利益。梁漱溟自认其动机纯正,但实践效果却对大众无益,反倒是助长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毛泽东在批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民族民主革命”,并强调“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这一观点源于对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准确判断,其深刻性不容置疑。
结语
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激烈辩论中,毛泽东坚守原则,但在策略上却展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使得梁漱溟感到交谈愉悦。梁漱溟回忆道:“那场辩论至今仍历历在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风范和气魄。他身着皮袍,或漫步,或坐下,或卧床休憩,显得轻松自在,从容不迫。他不失态,不激烈争辩,言辞幽默,不时抛出令人意外的精彩语句。尽管辩论激烈,却让人感到心情舒畅,仿佛老友间的谈心。送我出门时,天色已亮,他最后说:‘梁先生,你是个有心的朋友,今天的争论我们不妨暂时搁置,待来日再续。’这样的态度让我由衷敬佩。我发现自己若没有坚定的立场,只是一味联合他人,又怎能真正有用呢?最终发现,联合之事竟都落在了毛主席的手中。这正是他的统一战线策略——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孤立对手。”毛泽东的魅力不自觉地让梁漱溟也成为了他的联合力量。
拯救中国的力量并非改良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
网络炒股杠杆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